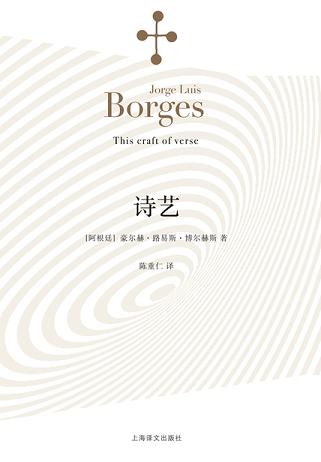
演讲集,一九六七年秋,博尔赫斯应哈佛大学诺顿讲座之邀,就诗的地位、隐喻模式、小说与诗、音韵与翻译等展开六讲。讲座录音带在图书馆尘封三十多年后,由时任西安大略大学现代语言文学系副教授的凯林–安德·米海列司库整理出版。全集广征博引,涉及从古至今诸多文学现象,又有着口语化文本的不拘形式感,娓娓道来,收放自如。“《诗艺》是一本介绍文学、介绍品位,也介绍博尔赫斯本人的书……博尔赫斯跟历代的作家与文本展开对话,而这些题材即使是一再反复引述讨论也总还是显得津津有味。”
诗艺 读后感《诗艺》是一本介绍文学、介绍品味,也介绍博尔赫斯本人的书。
1967年秋天, 已是公认瑰宝、双目失明的博尔赫斯来到哈佛开授诺顿讲座,谈诗论艺共6讲。
第一讲《诗之谜》于1967年10月24日发表,讨论诗歌的主体地位,有效引领听众进入系列讲座。
第二讲《隐喻》于11月16日发表,以莱奥波尔多·卢贡内斯为典范,探讨几个世纪以来诗人一再采用的同样隐喻模式,比如眼睛与星星、时间与河流、女人与花朵、生命与梦、死亡与睡眠、火与战火等,博尔赫斯认为这些隐喻可以归类为十二种“基本的典型”,其他的是为了达到惊人的效果,也就比较昙花一现。
第三讲《说故事》 于12月6日发表,对于现代人忽略史诗的情况提出建言,他思考了小说之死,并且提出当代人类的处境也反映在小说的意识形态里头:“我们并不相信幸福,这是我们时代的一大悲哀。”他在这里也表现出他与瓦尔特·本雅明与弗兰茨·卡夫卡思想上的相似之处(他认为后者跟萧伯纳与切斯特顿相比只能算是个小作家而已)。他倡导小说叙述的立即性,不过他的立场却也有点反小说,把他未创作小说的原因归罪于他的懒惰。
第四讲《文字—音韵与翻译》于1968年2月28日发表,据称是探讨诗歌翻译的大师之作。
第五讲《诗与思潮》于3月20日发表,探讨文学的地位,展现出他信步所至的风格,而不是理论思辨的方式。博尔赫斯认为魔术般的音乐真理比起理性思考的作品还来得强而有力,一味挖掘诗歌里头的意义是拜物的行为,他也认为太过有力的隐喻将会破坏诗歌的诠释构架,反而不会增添更深刻的意义。
第六讲《诗人的信条》于4月10日发表,是一番自我告解,是一种他在“活了大半辈子后”的文学誓言。
博尔赫斯的创作力在1968年间还处于高峰,他最一流的作品在那时都尚未发表,像是《布罗迪报告》(El informe de Brodie,1970年)收录了他自称最好的作品,《侵入者》(The Intruder)以及《沙之书》(El libro de arena,1975年)。
这些演讲的录音带被放在图书馆储藏室里囤积尘埃30多年才被整理出版。整个演讲较为轻松、浅显、幽默、谦逊、点到为止,对于诗歌初学者应该会有所启迪。
※第一讲 诗之谜
*诗和语言是一种“表达”(expression)。
*诗与语言都不只是沟通的媒介,也可以是一种激情,一种喜悦
*我会这么说:每当我们读诗的时候,艺术就这么发生了。
※第二讲 隐喻
*所有的隐喻都是建立在两个不同事物的连结之上
*“我们的本质也如梦一般。”
“我是梦到了我的人生,抑或这就已经是真实的人生了吧?”
*荷马……说过“钢铁般沉睡的死亡”
*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名诗:这里的树林是如此可爱、深邃又深远,/不过我还有未了的承诺要实现,/在我入睡之前还有几里路要赶,/在我入睡之前还有几里路要赶。
*“上帝峥嵘的面容,比起汤匙还要闪亮,/综合了一个毁灭性字眼的意象。”
*“一座如玫瑰红艳的城市,已经有时间一半久远。”
*“我要永远爱你,而且还多一天”
*莎士比亚也写过“四十个冬天围攻你的容颜”
*也可以找得到“刀剑相会”、“刀剑互舞”、
*还有一个不错的比喻:“愤怒之聚会”
*把战争称做“男人间的阵式”
*拜伦……这首诗:“她优美地走着,就像夜色一样。”
※第三讲 说故事
*“大海在船只的映照下远近散落一地,/就像是天空中的星星一样”(华兹华斯)
*“你的声音如音乐,你听音乐何以如此凄怆”
※第四讲 文字—音韵与翻译
*真理的精髓与真理的核心。
※第五讲 诗与思潮
*沃尔特·佩特说过,所有的艺术都渴望达到音乐的境界。
*《圣经·旧约》第一章就曾经提过:“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伟大的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一首短诗:“肉体上的老朽是智慧;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彼此热爱着,却是如此地无知。”
*乔治·梅瑞狄斯的诗作:“在壁炉的火焰熄灭之前,/让我们找寻它们跟星星之间的关联吧”。
*我们是先感受到诗的美感,而后才开始思考诗的意义。
*“越过明月的两朵红玫瑰。”
*乔伊斯:“如河流般,如流水般流向这里也流向那里。夜晚啊!”这是个极端的精心雕琢之作。
※第六讲 诗人的信条
*不过我的生命重心是文字的存在,在于把文字编织成诗歌的可能性。
*莎翁说过的,“你是音乐,为什么悲哀地听音乐?/甜蜜不忌甜蜜,欢笑爱欢笑”
*济慈在写下“美丽的事物是恒久的喜悦”
*文字是共同记忆的符号。
※论收放自如的诗艺
*他的眼疾持续恶化,到了一九六〇年左右就几近全盲,只能看得到一片橙橙的黄。整本《老虎的金黄》(El oro de los ligres,一九七二年)忠实呈现了他最后能看得到的颜色。
*博尔赫斯的演说方式很独特,令人叹为观止:他在演说的时候眼睛会往上看,他的表情温柔中又带点羞涩,好像已经接触到了文本的世界一样——文字的色彩、触感、音符跃然浮现。对他而言,文学是一种体验的方式。
*他在《诗艺》里头俨然就是荣誉贵宾的口气了,不但娓娓道来,更是收放自如。
*他的双亲更是精通英文(父亲是心理学以及现代语文的教授,而他的母亲则是一位翻译家)。
*博尔赫斯的学养绝对是相当深厚的,而他的作品主旨也经常明显地融入了自传式的成分——也就是学海无涯的主题。
*博尔赫斯的伟大有一部分来自他的才气机智与优雅精练,这种特质不但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更是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有人问他有没有梦见过胡安·贝隆,博尔赫斯反驳道:“我的梦也是有品位的——要我梦到他,想都别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