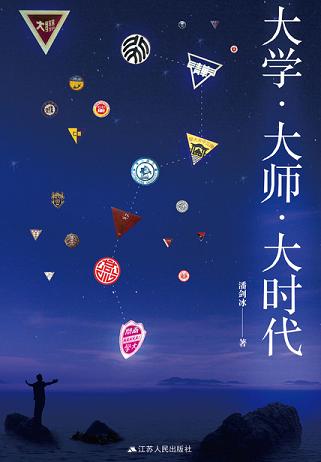
在《大学·大师·大时代》中,教师、学生、学校“三位一体”,内容有趣而又深刻,全面深入地讲述了民国时期的教育。《大学·大师·大时代》一书,从晚近以来海量的回忆录及相关史料等中挖掘整理出众多民国时期学人、学子之趣闻轶事,以此梳理、搭建出一条民国大学的精神脉络,勾勒出一张民国大学精神图谱,并力图重现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一百年来,以及五四运动爆发近百年来中国大学的“学统”,诠释大学存在的价值和大学之所以为大的核心要义。
大学·大师·大时代读后感大学,大师,大时代。为了方便起见,我把它简称为三大主义。其中,“大学”“大师”相对来说是微观的,而大时代却有宏观之意。
大学之光照耀过去与未来。短暂的四年,可能是一段提高自己最重要的时期,常怀热爱之心,无论是读书还是待人,都要用心,且用真心,最终把自己锻炼成真正有思想,有德行的人。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重要的不是到达旅途的终点,而是观赏沿途的风景,或修炼看风景的心情,求学亦复如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与师友的碰撞融合,学习中的喜怒哀乐,想象力、创造力、独立思考能力之生发,进而整个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这些都将使知识本身变成一种伟大的信仰,也是人类超越机器的地方。对于大学生涯的热爱,不仅仅是当年学子的集体情感,也是当年教师的普遍价值。
天地广阔,山河浩荡,最令人留恋的还是校园中的大草坪和林荫道。我们曾于此卧看云起,也曾执手走过落叶翩翩。惟有以此洁白纯净为底色,方可在人生的画布上泼洒出大写意。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以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寄托了一代学人的最高理想,寅恪先生有幸目睹了这种理想的盛景,也不幸亲眼见证了这种理想的幻灭。
天才也会成群地来,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曾经发出这样的追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对此,史学家王汎森的解释是学问境界的造就不仅需要师徒之间的纵向传习,还要有同辈之间的横向激发,两者缺一不可。
“清华四剑客”是季羡林、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联大三剑客”是杨振宁、黄昆和张守廉民国学术界盛产性格巨人,他们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内睥睨当世,谁也不服,要找个折服的对象只好照镜子。而且这些人都做到了言行一致,心里狂,嘴上也狂,其张扬与桀骜,犹如惊鸿照影,给民国的学术天空抹上了一块独特的亮色。
有句话说得好,老师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可悲的是,我们现在的不少老师从教后,桶里的水都处于一个不断蒸发的过程,水平与日俱退。
随着帝制终结,“家天下”的寿终正寝使得民国的学者们终于可以痛快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不必像乾嘉学者们一样躲进小楼、皓首穷经。群雄逐鹿的北洋军阀时代,也正是学术空气中自由负离子含量最高的时期。
人书合一,臻于至境。唯有青春与书籍不可辜负。国学大师黄侃好书成痴,自称“书痴”,而曾与他在中央大学共事的胡小石却称他“书淫”。中国的学生正在变得越来越“专一”:很多同学除了教科书,其他什么书都不看。据报道,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生对母校图书馆的回忆竟然是“路过”。或许大家若干年后再相聚,可以彼此聊以自嘲:那些想看而又没有看的书,在心中摆满了一座图书馆。
清华校长梅贻琦曰“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众多的民国学子虽然不一定了解梅贻琦的这句名言,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了梅校长。当年很多学生在升学时,往往注重的不是学校的建筑、专业的前途和路途的远近,而是在未来的求学中能不能遇到自己心仪的老师,能不能亲耳聆听大师的教诲。有无大师,已经成了学子们在衡量学校和专业的天平上最大的砝码。而这样的模式,已经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敬业的前提是惜业。显然,来之不易的东西更易为人珍惜。民国读大学是件奢侈的事情,一年开销少则百来块大洋,多则好几百大洋,穷人家的孩子哪里负担得起?因此,大家想当然地认为民国读大学的大都是“有钱人家”的子弟。
未来的大学,必定从现在的技术至上转向人本主义。归根到底,每个人的独一无二之处就在于他的思想,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棵会思想的芦苇”,德国诗人荷尔德林曰“人,诗意的栖居”,言下之意正是如此。